从人造怪物到人造新人 与机器人共存的美丽新世界
时间:2017-05-24 10:02:40 来源: 光明网
目前,围棋国手柯洁九段正在浙江乌镇迎战Alpha Go。与2016年由欧洲围棋冠军樊麾二段和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九段应战的两场“人机大战”不同,尽管我们仍旧期待这场棋盘上的较量,但似乎不再那么地渴望胜利,尤其不再那么地看重战绩背后的意义。
这或许是因为去年那两场分别以5∶0和4∶1告终的战局,使得原本那种对于“人类智慧”的莫名骄傲不再稳固。不过人类创造出了令自己备感沮丧的对手,这本身或许就是一个宿命。在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勇于颠覆自己的思想长久以来被人推崇。具体到机器人的复杂命题上,或许选择与机器人好好相处,共同打造美丽新世界,是通向未来的唯一路径。
人类败给机器人不是新闻,在日常生活中,人类的许多工作已经被机器取代了。但是,人类下棋输给了Alpha Go还是让人不禁唏嘘。细究这种隐约失落感的缘由,很容易让人想起二十年前的另一场颇为相似的人机大战。
1997年5月11日,由IBM公司生产的超级电脑“深蓝”,击败了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发生在二十年之前的这次人机大战,也一度被赋予了某种历史象征意味,仿佛人类与电脑之间的关系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
但在当时人类的眼中,国际象棋毕竟仍旧是一种规则相对复杂的游戏。它可能出现的棋局状况虽然也极多,但毕竟还是可以穷尽的。而围棋,纵横十九条直线,简单到极致的规则,却似乎仍是一种无法依靠数学建模来进行掌握的神秘游戏。棋盘上落子千变万化,许多时候必须依赖于人的智慧和直觉。因此,许多人相信,主要优势在于强大计算力的电脑,依旧会在这片充满哲学与美学意味的领地面前败下阵来。
时光荏苒,虽然最终的围棋人机大战胜负未定,但在2016年年底到2017年年初,Alpha Go化身为神秘棋手“Master”,在某围棋对战平台上连胜五六十局,将包括聂卫平、古力,以及柯洁本人在内的中日韩多国棋手统统斩于马下,这还是令人惊叹。1月4日,棋手真实身份公布后,举世哗然。这场机器的胜利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悄然到来,未来的图景徐徐在眼前铺展,那将是一个人与机器人共存的美丽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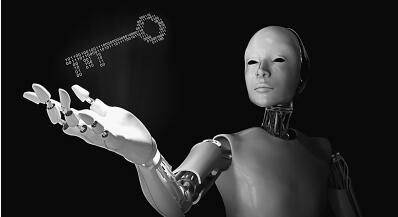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1·《弗兰肯斯坦》:人类造物的噩梦
最初感受到这一新时代先声的,是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人们。
在当时西方各国的工业革命已经相继完成,科学技术慢慢摆脱了“自然哲学”的陈旧命名,正在展现出自己那足以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人们一边崇拜着魔法般的科技,一边也为这已经豁然洞开的潘多拉魔盒感到隐忧。就在这一时期,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创作了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小说的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是一位天才科学家,他在拥有对于人体科学强烈好奇心的同时,表现出了浪漫主义英雄般的强大行动力。他先从坟地里取来材料,把它们缝合拼接成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然后又从暴风雨中引来闪电,赋予了怪物以生命。然而,这个特殊的人造人并不能为世人所接受,在经受殴打,到处遭遇偏见、歧视,甚至被它的创造者所抛弃之后,他的仇恨之火终于点燃。怪物的复仇最终裹挟着科学家一起,走上了毁灭之路。
无论是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还是中国神话中的女娲,创造人类一直是世界各民族神话传说当中永恒的母题。当人类开始意识到科技那无与伦比的力量之后,最先引起兴趣的,也往往是想象如何利用它来创造生命。与此同时,这种僭越造物主权柄的行动,自然也会让人们心生忌惮,它的神秘和不可控总是会让人们隐约感受到某种可怕的灾祸就隐藏在黑暗迷雾之中。正如科学家在埋葬了死于怪物之手的至亲之后,哀叹道:“我灵魂深处发出了痛苦、恐惧和无望的呐喊。而他们,只不过是我亵渎神灵的技术所造成的第一批遇害者!”
一个富有深远意味的细节,是小说中的这个“怪物”始终没有名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命名”实际上是一种标志性的行动:它暗示着我们把一个陌生的事物接纳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弗兰肯斯坦》年代里的这种抗拒心态,背后其实隐藏着另一种更为深刻的恐惧:科技正在破坏我们对于“人”的自我定义,也正瓦解着此前维持了数十个世纪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个过程既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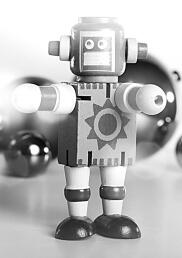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在工业革命当中,机器化大生产迅速地蚕食了手工业劳动者的生存空间。人们或者被改造成为产业工人,或者因此而失业。因此,在当时有不少人把大机器视为一切罪恶的源头。在英国诺丁汉等地,人们组织起来用捣毁机器的方式来抵抗近代工业技术,史称“卢德运动”。在这些运动背后的更深处,隐约透露出当“人”和“人性”在现代科技面前不断瓦解之时,普罗大众所产生的深刻焦虑。《弗兰肯斯坦》的创作与这场运动大致同时,天才科学家也从此成了一个科技时代里的隐喻,承载着人们对这日新月异的世界的恐惧。
然而科技的力量终究无法抵挡,无论人们看待它的眼光如何,工业革命早已如同那飞驰的火车,击碎瓦尔登湖畔的宁静,呼啸而过。
2·《我,机器人》:会出故障的工具
在《弗兰肯斯坦》之后,人类对科技的乐观接纳持续许久。尤其是在凡尔纳等著名科幻作家的笔下,被科技武装起来的各色人等,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新时代的全新英雄形象。虽然弗兰肯斯坦先生所面临的焦虑依旧徘徊不去,但在此时,人们开始倾向于承认人类的科技造物在生活当中占据的位置。在这一时代被反复状写的机器人,则是诸多人造物形象的集中体现。
1950年,美国著名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中短篇科幻小说集《我,机器人》。小说中不但有机器人,还有名为苏珊·凯文的“机器人心理学家”。小说集描绘了一幅未来世界中人与机器人共生的图景,展现了机器人的智能水平在经历了一步步发展之后,最终“挺立于人类与毁灭之间”。
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即是在这部小说集中提出的: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旁观;
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除非该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
第三定律: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
在阿西莫夫的故事中,尽管三定律在约束机器人的行为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状况——这也是“机器人心理学家”的职责所在:有意思的是,她要做的并非排除“故障”,而是要理解和解决机器人的“心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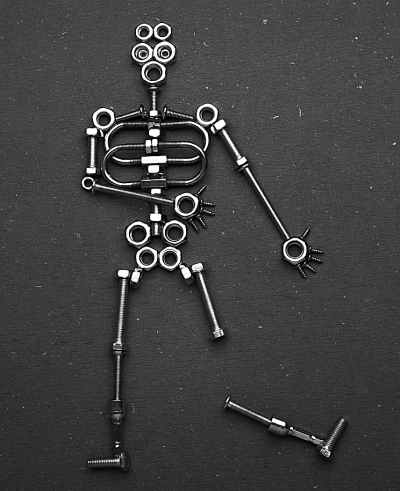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人的想象中,机器人固然是一种强大的工具,但它偏离自身“定位”的可能性则随时存在。小说家们在想象人类的工业化未来之时,既给机器人留出了系统性的定位,又时刻表现出对这种工具的防范。实际上,“机器人(Robot)”一词首先便来自于1920年捷克作家卡雷尔·卡佩克的科幻剧本《罗萨姆的万能机器人》,它的来源是捷克语“Robota”——这恰恰是“奴隶”的意思。在卡佩克的故事中,机器人由于不满人类的奴役,最终奋起反抗,消灭了人类:这几乎就是此后数十年间,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人与机器人关系的基本框架。一方面,人类不得不承认机器人有“保护自己的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着这种需要可能会在故障当中被放到前两条定律之前:到那时,“奇点”或“机器人革命”便会到来。
科幻小说中这种焦虑,有着极为真切的现实来源,这就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它们客观上刺激了科技进步的同时,更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伤痛。在其过程中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也在战争的催化中不断地异化为一只危险的巨兽。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同,现代战争中武器的杀伤力增长了何止千百倍。战争对人类施加伤害的方式也变得更加残忍,奥斯维辛等集中营之所以变成一种人类文明史上的伤痛,恰恰是因为它背后的逻辑,乃是以一种高度理性化,甚至堪称工业化的方式运作的。如果说工业化是文明的产物和标志,那么当它展现出危险的力量时,人们又该如何面对?那些在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军人和科学家们,不少将他们那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对核战争的焦虑,在那个年代以科幻小说的方式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表现。
人与人造的机器在不断地摸索中磕磕绊绊地扶持前行,试图找到一条可以和谐共生的道路。但与玛丽·雪莱笔下那个自始至终连名字都没有的人造怪物不同,阿西莫夫的机器“人”至少已经成为人类可以利用的工具。“它”们已经能够拥有一个代号——比如“终结者”“霹雳五号”或是《星球大战》里的BB-8——比起《弗兰肯斯坦》中的人造怪物,它们在成为“人”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使这些工具有时显得不那么靠得住,人类也仍然需要它们去完成一些前所未有的工作,进而达成前所未见的功绩。
3·《超能陆战队》:疗救灵魂的伴侣
在五十年代,以“心理医生”去“治疗”机器人,已经是跨越时代的狂想。但放到今天,我们似乎已经能够毫无障碍地开始想象,人类普遍地从我们的人造物身上寻求情感安慰的场景,我们有时甚至把更加重大的任务——比如拯救人类——放到“他”们肩上。
2015年热映的《超能陆战队》(Big Hero 6)是这类故事的典型。主人公小宏的天才哥哥意外丧生,他生前发明的治疗型机器人“大白”在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也成为小宏终日相随的伴侣。
“大白”不仅可以为人们治疗身体上的病痛,更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抚慰了小宏的心灵。圆滚滚的外形,呆萌的动作,温柔的个性,为整部电影都笼罩上了一层温情的色彩。这样一个机器人的形象,早已不是连名字都没有的怪物,自然也无法被简单地看作工具:他是一位最忠诚的朋友,甚至充当了人类的保护者和情感的寄托。
除了“大白”之外,类似的机器人形象数不胜数。从《机器人总动员》里的伊娃和瓦力,到更早《两百年人》里的机器人管家,再到《人工智能》里的小男孩,甚至是《宇宙静悄悄》里的五边形机器人。他们的形象虽然还主要被呈现为人造的“他者”,但却总是在频频越过物与人之间的模糊界限。这种“过界”有时被描绘成机器人自身的觉醒,有时被视为机缘巧合之下,人类自己的选择。
但更值得注意到的是,当人造物不再是单纯的“物”,那么造物的“人”自然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大白和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放在一起,同样是人造物,他们在力量、智慧方面其实很难说有什么本质差别,而外部视觉形象上的疏离与接纳,反映的则是两百年间我们人类自我定义的深刻改变: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人造人”——人造“物”——来定义我们个体与群体的成就。机械早已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人,则已经成为新人。
这便是围棋人机大战,以及“奇点临近”的深刻历史意义。虽然虚构作品当中那种转载了强人工智能的终极版人造人还没有最终出现,但人类智力所受到的全方位挑战从未如此严峻——至于体力方面,从两百年前就早已放弃。
有趣的是,我们对于挑战者似乎早已抱有一种颇为天然的接纳和依赖。在我们所熟悉的、每天都被电脑和智能手机所环绕的生活里,与人造机器的共生本就是我们生命体验的一部分:这便是现实的生活状态。







